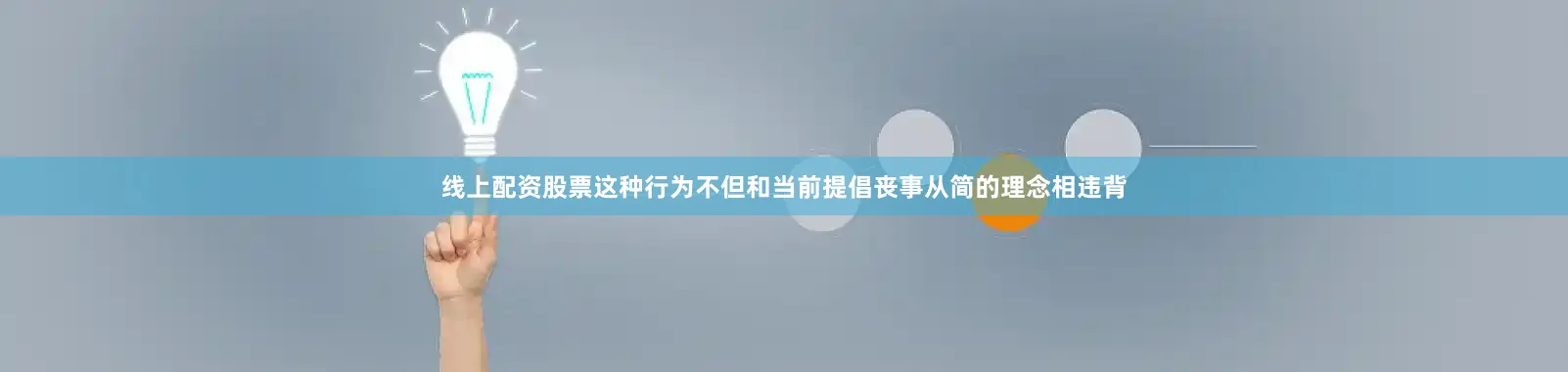把致敏花粉和杨柳飞絮的治理防控写入新法,也再次表明,民众的焦灼与期盼就是政府治理的靶标和方向。

资料图:工作人员对北京街头的桧柏洒水喷淋,以减少花粉飘散量。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
文 | 胡栖安
花粉过敏,有“法”治了!
据报道,9月26日进行的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〉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。其中,致敏花粉和杨柳飞絮的治理防控被写入《办法》。《办法》也规定了区人民政府,市园林绿化、气象以及林业经营者等各自的职责。
当下正值秋季,对于过敏人群来说,打喷嚏、鼻涕停不住,眼睛痒痒流泪等情况并不少见。前不久,“北京今秋花粉季提前来临”话题还登上热搜。在此背景下,北京将花粉治理写入新《办法》,无疑是对市民需求的精准回应。
近年来,花粉过敏已成为城市易感人群的梦魇,每年都要“遭二茬罪”,春季花粉期刚过,秋季花粉期又来了,这种“呼吸之痛”困扰了不少人。以北京为例,全年花粉期呈现在3月-4月和8月-9月两个高峰,这使得不少人错过了北京最美的春秋两季。
民众的焦灼与期盼,是政府治理的靶标和方向。近年来,北京市治理花粉的脚步也没停。不仅气象部门及时发布花粉浓度检测数据,医务工作者提醒潜在患者提前预防性用药,避免花粉高峰期出现严重症状,园林绿化部门也在研究如何通过物理和生物等措施,尽可能减少花粉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。
以北京圆柏而言,据披露,北京农学院的科研团队已研发出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花粉固定剂,能有效遏制柏树花粉飘散。该成果有望明年率先在北京市西城区、东城区、朝阳区等6个区使用。
然而,尽管花粉治理力度不断加大,但短时间内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毕竟,花粉传播是植物繁衍生息的自然现象,人类与植物相伴相生,只要植物存在,自然也就不可能把所有的花粉消灭。花粉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,远超人们想象。这也意味着,这项工作需要不断探索,久久为功。
此次《办法》的通过,无疑给相应的治理工作开出了药方。
一方面,《办法》提出“林业经营者应当采取树种更新改造、物理和生物防治等措施,加强治理防控”,这体现了靶向治理的思路。既然北京春季花粉期以木樨科、松科、柏科树木花粉为主,秋季花粉期以杂草花粉为主,那么,相应的治理当主要围绕这些树种和杂草展开。
事实上,北京市已开始尝试更新树种。据媒体此前报道,修订后的《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》就删除了刺柏属植物。不过,人为干预工作也要建立在审慎的基础之上,充分评估更替去留带来的次生生态问题,特别是要避免简单化“一砍了之”的思维。
另一方面,《办法》也提到“建立健全致敏花粉和杨柳飞絮综合防治工作机制,开展防治技术研究”。这也表明,必须充分认识到人与植物、城市与植物的互动关系,综合施策,重在预防。
据媒体报道,花粉浓度也受局部环境影响:在郊区软质地面(如土壤)上,花粉沉降后不易再次飘起;而在城市硬质地面上,沉降的花粉可能因热空气上升而再次悬浮,形成花粉浓度的第二个高峰。基于此,城市建设不妨对植物更友好些,尽可能多增加软质地面供给。
花谢花飞花满天,春日里,有飞花,也有飞絮;八月秋高风怒号,秋日里,各种植物的花粉随风飘散。这些在传统中一向颇有诗意的自然现象,如今却成为困扰人们呼吸道的问题,这也让人们再度审视人和植物的关系。
民之所需,政之所向。研究花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,而是要着眼于跨部门协同、跨学科联动、长时段关注、系统化破解等。如今,随着花粉治理等工作写入新法,让这一工作有了新的抓手。相信随着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,必将为市民创造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。
撰稿 / 胡栖安(媒体人)
编辑 / 马小龙
校对 / 张彦君
欢迎投稿:新京报评论,欢迎读者朋友投稿。投稿邮箱:xjbpl2009@sina.com评论选题须是机构媒体当天报道的新闻。来稿将择优发表,有稿酬。投稿请在邮件主题栏写明文章标题,并在文末按照我们的发稿规范,附上作者署名、身份职业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以及银行账户(包括户名、开户行支行名称)等信息,如用笔名,则需要备注真实姓名,以便发表后支付稿酬。
配资实力股票配资门户,亿米网,北京正规的股票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在线配资炒股售价为原油的2–3倍!通过管理原油开采与水源供应
- 下一篇:没有了